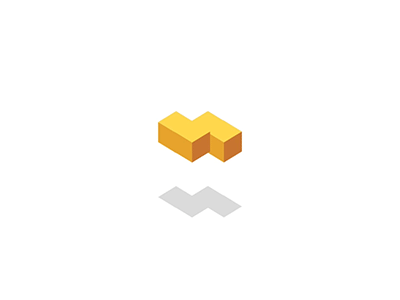看到我們的《辭彙》於1967年出版後被譯成十五種語言左右,自然感到欣慰。然而,在陳教授與沈、王兩位先生等人的細心照料下,今日中文版的問世為我帶來的卻是一種全然獨特的喜悅。
以中文……。我想是尚.考克多(Jean Cocteau)轉述了畢卡索這個敏捷的回答。在畢卡索的畫前,一位女士以時常伴隨著愚蠢的自信,驚嘆道:「哎呀,完全不懂。難以理解(c'est du chinois. 這是中文)」。對此,畢卡索反駁說:「親愛的女士,中文是一種六億人說的語言」(這應是當時的數字)。
佛洛伊德最初的作品引起同一類的反應,儘管它們不是以相同的字眼表達:荒謬、可恥、無法理解。一如畢卡索,佛洛伊德回答道:「這個你所棄絕的語言,卻正是數百萬人,甚至是所有的人類所說的語言。這是無意識的語言;我竭盡全力使它得以理解,翻譯它──這個陌生、神秘、尤其比其他語言都來得更為生動的語言」。那麼《夢的解析》這部精神分析的初書,若非是對我們的夢與症狀這種「中文」的辨讀,還會是什麼?
新譯本的刊行,也讓我有機會在三十年後就這項需要多年工作──一項因為加深了一段長久的友誼而更令人高興的工作──的計畫所代表的一切,提出幾點評語。
第一點:尚.拉普朗虛與我兩人時常因下列的現象感到惱火:我們的《辭彙》在某些外文版中被稱作《辭典》或,更惡劣地,《百科全書》,就好像我們允諾我們的讀者:「現在你將完全理解精神分析!」的確,辭彙與辭典之間的細緻差異或許似乎微不足道:兩者不都是以字母順序分類的方式,清點整理了日常或專門語言中的字?然而對我而言,兩者之間確實存在一種根本的差異:辭彙,正如其名便足以表示,所針對的是由一社會群體或一個人所確實使用的語彙;例如,我們可說:它豐富或貧瘠。就作者而言,它僅限於抽取出他藉以表達他所想說的話的那些字。將此特徵更推進一些,我們可以肯定地說,辭彙與語言辭典不同,前者所關切的並不在於所有現存的字,而在於一個群體或一個個人賦予其特殊意義的那些字。
這帶領我到第二點。雖然我們的序言說明的很清楚,但某些讀者還是抱怨我們的著作中並未列入包括「夢」、「焦慮」或「愛」等條目。就好像在佛洛伊德的著作中存有一種對夢的創新構想,一種甚或多種焦慮理論,在他之後我們便不再如往常一般理解愛這個字;然而,儘管如此,人們並不因此就暫止不去作夢、愛、恨、或理解焦慮。這些字與現實早已存在許久。明顯地,《辭彙》的目的從來不在於提供一本精神分析手冊,讓人不必閱讀佛洛伊德的著作。它力求引介人們進入佛洛伊德的著作中,並提供一些標記、要點;我必須補充,對我們兩個作者而言,它的意義也正是如此:它是一種研究,而非是先前獲得知識的一種應用。反之,作為對我們而言一種朝向佛洛伊德的運動之回音,我們希望能夠說明我們所分析的概念之運動,這些概念在著作中移置,朝向多種不同、有時甚至相反的方向。這些方向變得豐富,但有時卻變得比它們初現時貧瘠。況且我們所強調的是評註而非定義:前者凸顯出此種思維的運動,而後者在獨厚一個意義的同時犧牲了多義性。
我所專注的正是此種多義性,或者用一種較簡單的字眼表示,這一開展系列的意義。由此引申出我對將精神分析語言變成技術性、專門語言的作法,抱持遲疑的態度:如此的語言,極可能使那些無法掌握它,繼而逸離的人退縮,因為他們只看見一種行話、一種語言牢籠;但精神分析是開放的!我認為,一如所有偉大的作家,佛洛伊德的確特別曲折,甚至顛覆他所使用的字──例如,抑制、投資、對象──然而這些字來自於日常語言,一種共享的語言。我們不要將精神分析語言變成「中文」!它屬於全人類。
讀者無疑地會察覺到,大部分摘錄在這本書中的佛洛伊德文本屬於後設心理學的範圍。它幾乎未提及較為「文學性」、但並不因此便較不「精神分析的」作品,如〈有關衛城之記憶障礙〉或〈無常〉。這是因為我們希望將討論集中在──這也是《辭彙》刻意的限制之一──那些被我們稱為佛洛伊德的理論裝置上。藉由一種更專注於文本而非營造作品的閱讀,其他研究者得以發現某些「意符」的重複出現,或彙整出佛洛伊德所特別強調的隱喻。我們的《辭彙》或許開啟了這些研究途徑。
最後,一個給讀者的忠告:當你們在閱讀佛洛伊德或其後繼者的著作碰到問題時,再參考這本書。尤其,我重複,不要將它當作一本手冊,不要認為藉由修習它你們便可環遍精神分析(永遠不可能結束精神分析!)。另外,當你們作為臨床醫生、哲學家或文學愛好者的經驗,變得足夠豐富與個人化,得以讓你們或許不自知地找到一種專屬於你們的思考與陳述方式、一種同時私密與開向他者的語言時,那麼就忘記這本《辭彙》吧!
尚-柏騰.彭大歷斯
在线听书:精神分析辞彙